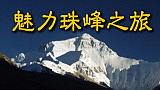西藏-作為肉身的酒
《序》
酒或者是作為蠱惑人心的東西而存在的。
關於酒後的不幸與失控每秒都流傳於你我口中,不同的方式,嘴也是個神奇的東西。
那位俠氣沖天的古龍某個夜晚倒在街邊的一灘水中,那時的他什麼感覺,酒?
感覺酒是小水,小股縱橫奔流的水,從你的口到我的口。
波波是愛酒的,雖然酒量和我一樣不濟,但還不至有飯必有酒。下次看他看來該帶點
酒。他那孤單而小的居所實在該有點酒方能驅除某些東西。
老雪也是愛酒的,每次看著酒在杯子裡多了又少,少了又多,其情緒也隨之起伏,直至高峰。然後說:每次總是我來收拾殘局的。
每次李大嘴總是要酒喝,每次總是不省人事,我負責善後。老雪說。
其實老雪更愛酒,如果沒有我提出:走吧。這酒我知道可以喝到天亮。
物質生活的瑪愛酒,和尼古拉斯一樣。
我不想說酒不是什麼好東西,很想說,也更有理由說。以前的輔導員勸我寬容些,於是我寬容了酒。儘管不情願。但總該越來越成熟,對吧?
《草原》
有的人寧願躺在床上讓無意識在空中隨意飄忽,窗外的人群越來越模糊,街道和建築的邊緣淡去,一個關於牧羊人的故事斷斷續續,若有若無。這種靠近草原的風險在於某個
人或某個電話的突然打斷。但顯然他是成功的,草原的某種質素就在於此,草原是飄忽的。易碎的。
一天在朋友的朋友家中,無意看到一封信的開頭:你還在飄著吧。
我是為了草原而去西藏的。蒙古人一定在笑,他們有理由笑,但是苦笑。博爾赫斯說蒙古征服中原後,企圖將整個中國變為草原,他們為什麼不這麼做呢,我也在苦笑,如果真那樣我也沒必要逃學去看什麼草原,還跑錯了方向。
同樣,如果不是某些原因我寧願躺在自己的床上想念草原,想像他的廣大,牧羊人抽著鞭子趕著牲口且不用上學,在這裡,逃學是懦弱的表現,可見大多數人都是勇敢的。可以想像他們騎在馬上威武的樣子,畢竟經過騎馬民族的教化。
但草原是美麗的。站在草原上我想躺下,我是那種不適合站的人,只要有機會就想找個地方躺下或坐著,何況在草原。
我軟弱得想躺下。
藏阿佳在寬大的草原面朝西天,一次一次地向下撲去,旁邊站著的是她的孫子吧。身後羊群一片一片,那是羊嗎,還是雲的影子?
我看見雲上映著雲的影子,天空藍。
我接觸不到阿佳的眼睛,甚至孫子的也不行。
司機叫我上車,沒有躺下,裝著躺下也沒有。
草原的人們愛著自己的地方就像23歲之前的我愛著戀人的彎眉毛。
感覺自己來到了波波的地盤,如果現在站在草原的人不是我而是波波,一定說:朋友,借草原用用,借你的馬用用,於是,偌大的草原上黑馬縱橫,那飛奔的不是一個靈魂而是一陣風,一團黑色的火。
這條彎月的河流叫阿木柯,一個看起來傳說中才有的名字,阿木柯彎向遠方,分割了草原。草原脆弱,嬌柔。讓人心也漸漸彎下去。
我們的車行進於草原中。在默默無語的傳說中穿行,像重巨大的幕在我們的去路。草原極處的雪山是不語的巨人,多少人打馬走過,趕著犛牛走過。
穿著紅衣的僧人推著一輛新的自行車對過,眼裡似曾相識的目光讓我覺得是兒時的玩伴,不是什麼唸經的喇嘛。
三輛東風大卡靜靜地走著,黑夜一樣寂靜的原野。
可惜那時的我既不知道騰格爾也不知道亞東,不知道草原人如何歌唱草原,直到三年後在波密的叢林裡在東風大卡的貨車廂裡在雨裡小聲地哼起了《蒙古人》,和那小子一路高歌《格薩爾》不能相提並論。但此時還有王洛賓和鄭均,還有《在那遙遠的地方》和《回到拉薩》,鄭均非草原正宗,他的歌就非草原人對草原的艷羨而言達到了極致,這一點《爬山》也做得不錯。
王洛賓背棄了漢,投向遠方。和三毛同樣熱愛著他的人不在少數,不知道草原人對他作何種程度的認同。
我曾答應在怡生日那天唱《在那遙遠的地方》,後來似乎沒唱,這歌屬於憂鬱者,而我們有的儘是快樂。奇怪的是,當她翻開海子的第一頁就喜歡上了,這是我沒有料到的。
如今,我在悲涼高亢的長調底下回憶草原,眼前卻沒有草原,草原早被揉碎,擠到看不見的肉身裡頭。
95年夏天,回到曾經呆過的學校,對面寢室的不眨眼地望著我,突然說:你身上有股野性。我彷彿被某個東西擊中,與生俱來的吧,如是想。
95年春天,我指著牆上那幅中國地圖說:瞧,這些叫錯的地方都是湖,藍色的,這地方有這麼多水卻如此荒涼,將來我會去的。
沒有等到將來。
我曾對鋒說:我快不行了,也許只有找個女人才能解救,但那時的他也不行了。我們如此相稱,沒有誰發現對方的問題。
在春天將要跨進夏天的一瞬,我走了。先波波而走。
那時的波波在什麼地方呢?
那時的波波在想些什麼呢?
走了。在校外的那間小屋裡,他們將看到一些碎紙片,上面只寫著一個字:雪。
本來是帶著本子上路的,以為能記下些什麼,從第一天開始便放棄,如果現在還記日記-站在混亂的車廂裡,站在草原的中央,坐在司機旁邊,也許我是來記日記的,而不是去西藏。西藏是個動詞,我喜歡這種理解。
我更喜歡後面那輛車的司機,可他帶著他的侄子。這個老西藏說:我有兩個身份證,一個重慶,一個日喀則。如果西藏獨立,我就是歸國華僑了。我不知道,但喜歡他的直白,他的閱歷。他說:你應該把一路所見所聞記下來,我保證西藏之行你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我沒有記下什麼,卻忘不了這地方。什麼地方? 不是,是這一路。
我常說,西藏不怎麼樣,但去西藏的一路很是怎麼樣。聽我講訴的人弄不明白。
他們大約是沒想到森林吧。
我也搞不懂為什麼有人這麼說:《重慶森林》。那是因為《挪威森林》,有人說。也許吧。王家衛也許這麼想。我不這麼想,就像你也不這麼想。
你想起雲的影子不是因為雲。
同樣,我去西藏不是因為地圖上漂著的那些錯。
而是因為波波。
我在走波波沒有走過的路,走在路上時突然想起。他是草原人的兒子,窮人的兒子,瘋子的兒子,而我不過是他的影子,他借了我走他的路。
草原屬於波波,屬於海子,不屬於我。我後來痛苦地回憶。
但草原美麗,我不增之,也不減之,他們也這樣痛苦過嗎?不得而知,他們或者沒有我這樣的自私吧。
草原依舊美麗。
95年的美麗與00年的美麗不同。95年的草原是和佛住在一起的人,00年住的是傳說中的牧人。5年後我變了,草原沒變,也許變了吧,誰知道呢,5年,足夠使你頭頂那顆星星的光變成你眼中的光。
5年過去,波波依然沒有來到這屬於他的領地,也許他不會來了吧,既然是他的就是他的,不是我的就算來得再多也沒敢騎上波波的那匹黑馬,據說騎上這匹黑馬穿過草原才是真的穿過草原,但這是主人的權利,我只敢遠遠的望著他的獸。人不能無所畏懼。那對我抽刀的漢子為什麼抽刀呢,一定是那一刻想起了什麼還是畏懼了抽刀的習慣。
00年, 我躲在老雪的背後像隻羊從北方的南方到南方的北方,我習慣於躲在某人的背後或者自己的背後,這次有了老雪,當然是她站在前面。我?不過是草原的看客。
草原依舊荒涼而大。
居然趕上千萬頭犛牛和黑帳篷(某司機說黑帳篷是藏人,白帳篷是蒙古人,黑帳篷是方的,白帳篷是圓的)的即興表演。無數頂帳篷整齊地圍著巨大的夏湖(冬草夏湖)形成的肥美的草灘,犛牛在天地搭成的舞台上盡情表演,用他們的嘴。
有比雙眼的視野更寬廣的相機嗎?如果有的話,也許能拍下來,我們沒有,這是我唯一一次想起燒貨的相機的時候。
三輛東風大卡排著隊穿越草原。前面的車突然停下來了,這輛車的司機以為前面出事了,急忙跳下車跑過去。
他說是藏民攔車。一會兒看到一個女人和她的孩子們揀去路上的石頭陣後向丈夫揮手告別。這告別熟悉又陌生,是誰發明了揮手,中原?西域?還是草原人?也許是上帝吧,上帝不號稱什麼都是他的嗎?
到底是草原,攔車也酷。98年,我學到了攔車的正宗手法:豎起大拇指,胳膊向路中央一伸,但奏效的時候少,比起這種方法差得太遠。但人家是人家,咱是咱,不能學的就是不能學。
我說草原,以前更多的希望是呼倫貝爾,或者蒙古之外,但我不是世界公民,紅原和若爾蓋就不錯了,再加上山與山之間的一小塊有和沒有犛牛行走的地方已經心滿意足。
點燃了一支煙就又想起了波波。
他淡淡的笑容讓我夜不能寐。
如果不擺脫他的陰影便無法繼續前行。
曾經和廣子常常談起他。後來看了佛洛依德和容格知道那時的我信心不足,現在的我依然信心不足。現在的我不再歌唱戀人的彎眉毛,心底裡又開始迷戀別樣的東西,這是不能讓人容忍的。
但不管怎樣總該擺脫了,記得帶酒給他就行了。
每天總得翻開新的一頁,換一種說法就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對嗎,老毛真偉大,深刻的道理到了他的嘴裡居然淺顯易懂。
我對某人說過,紅原是藏族人的領地,我到的第一天就明白了,就是這樣,我們的司機還是撞倒了一根電線桿,年輕的鎮長一毛一分地算出了這跟電線桿的價錢。
草原的故事在藏人的心裡頭,我卻在這裡講什麼草原。有點搞笑,但搞笑的事情很多,在搞笑的世界裡頭這是件頂不搞笑的,對吧。
我就知道寫到某個時候就想撤,也想和這種想法較一回真,就算我是個不較真的人。
用筆,草原是無法接觸的,只可能以各種方式接近。草原留給我的只能是回憶,既不是巴特零碎紛亂的思緒也不是克爾郭凱爾關於建構的可怕分析。草原就是草原。
但草原是飄忽不定的,玄想者大都同意這一說法,或者說,草原天生具有適合玄想的某種質素。就說草甸子吧,什麼是草甸子?對於植物學家這不是個問題,但不論對於牧人,詩人,遊蕩者,或是玄想者這是個大大的問題,正是因為概念的不確定性決定了草原上方的空氣中有某種東西在飄蕩。從某個角度來看,遊蕩者比牧人更接近草原,這個推想使我有些安慰,同時,波波的影子再次從眼前閃現。
我點燃了另外一支煙,和煙霧一起騰升的是某種和嘴裡一樣淡淡的苦味。
海子似乎沒有寫關於草原的詩,即便某幾首詩中提到了「草原」,這似乎和他走過的路線無關。
荒原屬於行吟者,草原屬於玄想者。
草原無法再現。得出這樣的結論未免讓人悲哀,這粉碎了許多人曾經或正在進行的工作,包括我現在做的。
不妨這麼說:草原過於完美,沒有缺憾的東西用人間的語言無法描述。
沒有人哭,沒有人笑,甚至沒有經幡的搖曳。
寂靜的草原。
黑水河再度分割草原,灌木再度分割河水。
河水是草原的詩章,灌木則是詩章的音節。
就像藉著雪山聖湖講述我的純潔一樣,我也藉著草原的飄忽講述不可捉摸的無意識。
回憶可以替代草原嗎,該死的克爾郭凱爾壞笑地看著我,他從不去草原卻用壞笑冷冷地剖析我回憶的走向,他破壞了我關於草原關於傳說的最初構想。
我決定退回成都-留守之地,出發之地。讓別人繼續我未完成的旅行,誰能堪此重任呢,因為這旅行對我來說稍顯沉重,換個人,也許換種構想的方式,不會被克爾郭凱爾之流所干擾。
呵呵,我已想到了最好的人選,至於我,可以找個小酒館,背靠成都,讓劍休息。
成都的酒是不錯的。
重量級人物登場。
你可以把前面作為波波出場之前的花絮,我想你已經把前面作為花絮了吧,呵呵。
可我有點猶豫了,這猶豫源自心有不甘,草原之旅對我是稍顯沉重不是非常沉重。
但不管怎麼說,波波已經做好準備了,容不得我現在反悔。
酒或者是作為蠱惑人心的東西而存在的。
關於酒後的不幸與失控每秒都流傳於你我口中,不同的方式,嘴也是個神奇的東西。
那位俠氣沖天的古龍某個夜晚倒在街邊的一灘水中,那時的他什麼感覺,酒?
感覺酒是小水,小股縱橫奔流的水,從你的口到我的口。
波波是愛酒的,雖然酒量和我一樣不濟,但還不至有飯必有酒。下次看他看來該帶點
酒。他那孤單而小的居所實在該有點酒方能驅除某些東西。
老雪也是愛酒的,每次看著酒在杯子裡多了又少,少了又多,其情緒也隨之起伏,直至高峰。然後說:每次總是我來收拾殘局的。
每次李大嘴總是要酒喝,每次總是不省人事,我負責善後。老雪說。
其實老雪更愛酒,如果沒有我提出:走吧。這酒我知道可以喝到天亮。
物質生活的瑪愛酒,和尼古拉斯一樣。
我不想說酒不是什麼好東西,很想說,也更有理由說。以前的輔導員勸我寬容些,於是我寬容了酒。儘管不情願。但總該越來越成熟,對吧?
《草原》
有的人寧願躺在床上讓無意識在空中隨意飄忽,窗外的人群越來越模糊,街道和建築的邊緣淡去,一個關於牧羊人的故事斷斷續續,若有若無。這種靠近草原的風險在於某個
人或某個電話的突然打斷。但顯然他是成功的,草原的某種質素就在於此,草原是飄忽的。易碎的。
一天在朋友的朋友家中,無意看到一封信的開頭:你還在飄著吧。
我是為了草原而去西藏的。蒙古人一定在笑,他們有理由笑,但是苦笑。博爾赫斯說蒙古征服中原後,企圖將整個中國變為草原,他們為什麼不這麼做呢,我也在苦笑,如果真那樣我也沒必要逃學去看什麼草原,還跑錯了方向。
同樣,如果不是某些原因我寧願躺在自己的床上想念草原,想像他的廣大,牧羊人抽著鞭子趕著牲口且不用上學,在這裡,逃學是懦弱的表現,可見大多數人都是勇敢的。可以想像他們騎在馬上威武的樣子,畢竟經過騎馬民族的教化。
但草原是美麗的。站在草原上我想躺下,我是那種不適合站的人,只要有機會就想找個地方躺下或坐著,何況在草原。
我軟弱得想躺下。
藏阿佳在寬大的草原面朝西天,一次一次地向下撲去,旁邊站著的是她的孫子吧。身後羊群一片一片,那是羊嗎,還是雲的影子?
我看見雲上映著雲的影子,天空藍。
我接觸不到阿佳的眼睛,甚至孫子的也不行。
司機叫我上車,沒有躺下,裝著躺下也沒有。
草原的人們愛著自己的地方就像23歲之前的我愛著戀人的彎眉毛。
感覺自己來到了波波的地盤,如果現在站在草原的人不是我而是波波,一定說:朋友,借草原用用,借你的馬用用,於是,偌大的草原上黑馬縱橫,那飛奔的不是一個靈魂而是一陣風,一團黑色的火。
這條彎月的河流叫阿木柯,一個看起來傳說中才有的名字,阿木柯彎向遠方,分割了草原。草原脆弱,嬌柔。讓人心也漸漸彎下去。
我們的車行進於草原中。在默默無語的傳說中穿行,像重巨大的幕在我們的去路。草原極處的雪山是不語的巨人,多少人打馬走過,趕著犛牛走過。
穿著紅衣的僧人推著一輛新的自行車對過,眼裡似曾相識的目光讓我覺得是兒時的玩伴,不是什麼唸經的喇嘛。
三輛東風大卡靜靜地走著,黑夜一樣寂靜的原野。
可惜那時的我既不知道騰格爾也不知道亞東,不知道草原人如何歌唱草原,直到三年後在波密的叢林裡在東風大卡的貨車廂裡在雨裡小聲地哼起了《蒙古人》,和那小子一路高歌《格薩爾》不能相提並論。但此時還有王洛賓和鄭均,還有《在那遙遠的地方》和《回到拉薩》,鄭均非草原正宗,他的歌就非草原人對草原的艷羨而言達到了極致,這一點《爬山》也做得不錯。
王洛賓背棄了漢,投向遠方。和三毛同樣熱愛著他的人不在少數,不知道草原人對他作何種程度的認同。
我曾答應在怡生日那天唱《在那遙遠的地方》,後來似乎沒唱,這歌屬於憂鬱者,而我們有的儘是快樂。奇怪的是,當她翻開海子的第一頁就喜歡上了,這是我沒有料到的。
如今,我在悲涼高亢的長調底下回憶草原,眼前卻沒有草原,草原早被揉碎,擠到看不見的肉身裡頭。
95年夏天,回到曾經呆過的學校,對面寢室的不眨眼地望著我,突然說:你身上有股野性。我彷彿被某個東西擊中,與生俱來的吧,如是想。
95年春天,我指著牆上那幅中國地圖說:瞧,這些叫錯的地方都是湖,藍色的,這地方有這麼多水卻如此荒涼,將來我會去的。
沒有等到將來。
我曾對鋒說:我快不行了,也許只有找個女人才能解救,但那時的他也不行了。我們如此相稱,沒有誰發現對方的問題。
在春天將要跨進夏天的一瞬,我走了。先波波而走。
那時的波波在什麼地方呢?
那時的波波在想些什麼呢?
走了。在校外的那間小屋裡,他們將看到一些碎紙片,上面只寫著一個字:雪。
本來是帶著本子上路的,以為能記下些什麼,從第一天開始便放棄,如果現在還記日記-站在混亂的車廂裡,站在草原的中央,坐在司機旁邊,也許我是來記日記的,而不是去西藏。西藏是個動詞,我喜歡這種理解。
我更喜歡後面那輛車的司機,可他帶著他的侄子。這個老西藏說:我有兩個身份證,一個重慶,一個日喀則。如果西藏獨立,我就是歸國華僑了。我不知道,但喜歡他的直白,他的閱歷。他說:你應該把一路所見所聞記下來,我保證西藏之行你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我沒有記下什麼,卻忘不了這地方。什麼地方? 不是,是這一路。
我常說,西藏不怎麼樣,但去西藏的一路很是怎麼樣。聽我講訴的人弄不明白。
他們大約是沒想到森林吧。
我也搞不懂為什麼有人這麼說:《重慶森林》。那是因為《挪威森林》,有人說。也許吧。王家衛也許這麼想。我不這麼想,就像你也不這麼想。
你想起雲的影子不是因為雲。
同樣,我去西藏不是因為地圖上漂著的那些錯。
而是因為波波。
我在走波波沒有走過的路,走在路上時突然想起。他是草原人的兒子,窮人的兒子,瘋子的兒子,而我不過是他的影子,他借了我走他的路。
草原屬於波波,屬於海子,不屬於我。我後來痛苦地回憶。
但草原美麗,我不增之,也不減之,他們也這樣痛苦過嗎?不得而知,他們或者沒有我這樣的自私吧。
草原依舊美麗。
95年的美麗與00年的美麗不同。95年的草原是和佛住在一起的人,00年住的是傳說中的牧人。5年後我變了,草原沒變,也許變了吧,誰知道呢,5年,足夠使你頭頂那顆星星的光變成你眼中的光。
5年過去,波波依然沒有來到這屬於他的領地,也許他不會來了吧,既然是他的就是他的,不是我的就算來得再多也沒敢騎上波波的那匹黑馬,據說騎上這匹黑馬穿過草原才是真的穿過草原,但這是主人的權利,我只敢遠遠的望著他的獸。人不能無所畏懼。那對我抽刀的漢子為什麼抽刀呢,一定是那一刻想起了什麼還是畏懼了抽刀的習慣。
00年, 我躲在老雪的背後像隻羊從北方的南方到南方的北方,我習慣於躲在某人的背後或者自己的背後,這次有了老雪,當然是她站在前面。我?不過是草原的看客。
草原依舊荒涼而大。
居然趕上千萬頭犛牛和黑帳篷(某司機說黑帳篷是藏人,白帳篷是蒙古人,黑帳篷是方的,白帳篷是圓的)的即興表演。無數頂帳篷整齊地圍著巨大的夏湖(冬草夏湖)形成的肥美的草灘,犛牛在天地搭成的舞台上盡情表演,用他們的嘴。
有比雙眼的視野更寬廣的相機嗎?如果有的話,也許能拍下來,我們沒有,這是我唯一一次想起燒貨的相機的時候。
三輛東風大卡排著隊穿越草原。前面的車突然停下來了,這輛車的司機以為前面出事了,急忙跳下車跑過去。
他說是藏民攔車。一會兒看到一個女人和她的孩子們揀去路上的石頭陣後向丈夫揮手告別。這告別熟悉又陌生,是誰發明了揮手,中原?西域?還是草原人?也許是上帝吧,上帝不號稱什麼都是他的嗎?
到底是草原,攔車也酷。98年,我學到了攔車的正宗手法:豎起大拇指,胳膊向路中央一伸,但奏效的時候少,比起這種方法差得太遠。但人家是人家,咱是咱,不能學的就是不能學。
我說草原,以前更多的希望是呼倫貝爾,或者蒙古之外,但我不是世界公民,紅原和若爾蓋就不錯了,再加上山與山之間的一小塊有和沒有犛牛行走的地方已經心滿意足。
點燃了一支煙就又想起了波波。
他淡淡的笑容讓我夜不能寐。
如果不擺脫他的陰影便無法繼續前行。
曾經和廣子常常談起他。後來看了佛洛依德和容格知道那時的我信心不足,現在的我依然信心不足。現在的我不再歌唱戀人的彎眉毛,心底裡又開始迷戀別樣的東西,這是不能讓人容忍的。
但不管怎樣總該擺脫了,記得帶酒給他就行了。
每天總得翻開新的一頁,換一種說法就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對嗎,老毛真偉大,深刻的道理到了他的嘴裡居然淺顯易懂。
我對某人說過,紅原是藏族人的領地,我到的第一天就明白了,就是這樣,我們的司機還是撞倒了一根電線桿,年輕的鎮長一毛一分地算出了這跟電線桿的價錢。
草原的故事在藏人的心裡頭,我卻在這裡講什麼草原。有點搞笑,但搞笑的事情很多,在搞笑的世界裡頭這是件頂不搞笑的,對吧。
我就知道寫到某個時候就想撤,也想和這種想法較一回真,就算我是個不較真的人。
用筆,草原是無法接觸的,只可能以各種方式接近。草原留給我的只能是回憶,既不是巴特零碎紛亂的思緒也不是克爾郭凱爾關於建構的可怕分析。草原就是草原。
但草原是飄忽不定的,玄想者大都同意這一說法,或者說,草原天生具有適合玄想的某種質素。就說草甸子吧,什麼是草甸子?對於植物學家這不是個問題,但不論對於牧人,詩人,遊蕩者,或是玄想者這是個大大的問題,正是因為概念的不確定性決定了草原上方的空氣中有某種東西在飄蕩。從某個角度來看,遊蕩者比牧人更接近草原,這個推想使我有些安慰,同時,波波的影子再次從眼前閃現。
我點燃了另外一支煙,和煙霧一起騰升的是某種和嘴裡一樣淡淡的苦味。
海子似乎沒有寫關於草原的詩,即便某幾首詩中提到了「草原」,這似乎和他走過的路線無關。
荒原屬於行吟者,草原屬於玄想者。
草原無法再現。得出這樣的結論未免讓人悲哀,這粉碎了許多人曾經或正在進行的工作,包括我現在做的。
不妨這麼說:草原過於完美,沒有缺憾的東西用人間的語言無法描述。
沒有人哭,沒有人笑,甚至沒有經幡的搖曳。
寂靜的草原。
黑水河再度分割草原,灌木再度分割河水。
河水是草原的詩章,灌木則是詩章的音節。
就像藉著雪山聖湖講述我的純潔一樣,我也藉著草原的飄忽講述不可捉摸的無意識。
回憶可以替代草原嗎,該死的克爾郭凱爾壞笑地看著我,他從不去草原卻用壞笑冷冷地剖析我回憶的走向,他破壞了我關於草原關於傳說的最初構想。
我決定退回成都-留守之地,出發之地。讓別人繼續我未完成的旅行,誰能堪此重任呢,因為這旅行對我來說稍顯沉重,換個人,也許換種構想的方式,不會被克爾郭凱爾之流所干擾。
呵呵,我已想到了最好的人選,至於我,可以找個小酒館,背靠成都,讓劍休息。
成都的酒是不錯的。
重量級人物登場。
你可以把前面作為波波出場之前的花絮,我想你已經把前面作為花絮了吧,呵呵。
可我有點猶豫了,這猶豫源自心有不甘,草原之旅對我是稍顯沉重不是非常沉重。
但不管怎麼說,波波已經做好準備了,容不得我現在反悔。
 MITS 美景國際旅行社
MITS 美景國際旅行社MEIJING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LTD
專門為台灣/香港/澳門等世界各地華人、外國人(外籍遊客)提供特色西藏、青海、
尼泊爾、四川等地度假觀光旅行服務,為您量身定制個性旅行計劃(獨立成團、小
包團、自由行、團體旅遊、散客拼團,另提供各類朝聖、徒步登山探險等特種旅遊)
外籍遊客進藏旅行須知:辦理台灣遊客入藏批准函.旅行證件.外國人去西藏旅行手續
Sponsored Links
特別聲明:
A:關於美景旅遊網獨立原創文章圖片等內容
1、美景旅遊網原創文章、圖片版權由我們全部保留;
2、美景旅遊網原創文章、圖片任何網站及媒體均可以免費使用,如轉載我們的文章或圖片,
請註明來自美景旅遊網 並鏈接到 www.mjjq.com,商業用途請先聯繫我們;
3、免責:我們在我們能知悉的範圍內努力保證所有采寫文章的真實性和正確性,但不對真實性和正確性做任何保證。本站采寫文章圖片如果和事實有所出入,美景旅遊網不承擔連帶責任;
B:關於美景旅遊網採用非原創文章圖片等內容
1、頁面的文章、圖片等等資料的版權歸版權所有人所有。
2、免責:由於採集的圖片、文章內容來源於互聯網,內容頁面標注的作者、出處和原版權者一致性無法確認,如果您是文章、圖片等資料的版權所有人,請與我們聯繫,我們會及時加上版權信息,如果您反對我們的使用,本著對版權人尊重的原則,我們會立即刪除有版權問題的文章或圖片內容。
3、本頁面發表、轉載的文章及圖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A:關於美景旅遊網獨立原創文章圖片等內容
1、美景旅遊網原創文章、圖片版權由我們全部保留;
2、美景旅遊網原創文章、圖片任何網站及媒體均可以免費使用,如轉載我們的文章或圖片,
請註明來自美景旅遊網 並鏈接到 www.mjjq.com,商業用途請先聯繫我們;
3、免責:我們在我們能知悉的範圍內努力保證所有采寫文章的真實性和正確性,但不對真實性和正確性做任何保證。本站采寫文章圖片如果和事實有所出入,美景旅遊網不承擔連帶責任;
B:關於美景旅遊網採用非原創文章圖片等內容
1、頁面的文章、圖片等等資料的版權歸版權所有人所有。
2、免責:由於採集的圖片、文章內容來源於互聯網,內容頁面標注的作者、出處和原版權者一致性無法確認,如果您是文章、圖片等資料的版權所有人,請與我們聯繫,我們會及時加上版權信息,如果您反對我們的使用,本著對版權人尊重的原則,我們會立即刪除有版權問題的文章或圖片內容。
3、本頁面發表、轉載的文章及圖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西藏旅遊
Tibet Travel
西藏旅遊目的地 
走進神秘西藏
西藏風光圖庫
熱門點擊 
最新旅遊報價